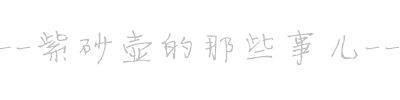许四海这名字不知是谁起的,但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人来说,那真是贴切准确、实至名归。书画界常讲“书如其人,画如其人”,许四海就是名如其人并壶如其人了。
许四海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是为壶而生、为壶而来的。
他玩壶较早,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部队时就已经喜欢了。他爱壶、买壶、藏壶进而亲手制壶,四十多年奋斗以壶而闻名于世。他纵横四海,四海纵横,过手的紫砂壶超过两万,收藏老壶一千多把。在那个年代,他做着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应做而没有做的事,非常了不起。一个记者问他:“你有‘供春壶’吗?”他说:“我没有。‘供春壶’只是个传说,目前还没见过。”他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在得令人可爱!

正是这个实在人创立了“四海壶具博物馆”,也正像那响亮宏大、内涵深刻的名字一样,他将四海之内各色紫砂壶等,尽其所能地收入馆中,成就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真正的第一家民间博物馆,立地沪上,光照四海。
几年以前,我曾数度走进“上海四海壶具博物馆”,也多次与许四海聚在一起。在他的“百佛园”博物馆内,始终是作为参观者,细细地浏览,慢慢地听讲,静静地观看,整个“百佛园”有塔有湖,有亭台楼阁,有小桥流水,有上千尊石佛伫立在大院之内,那规模不是常人可以简单想象的,那里的一切告诉来访者, “百佛园”的主人是一个重干而轻言、言必行、行必果的人。
几次接触,我发现许四海内敛大于外向,不属于见面熟一上来就热情洋溢的人。他是慢热型性格,我也恰恰不善沟通,于是我与他的正式交谈便一次也没有。今年春节过后,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在《收藏界》杂志社会议室里,为他举办“许四海藏品北京鉴赏会”。会议间隙记者采访,我也只是陪坐在一旁,听他们一问一答而已。其实我们有过两次相约面对面促膝长谈的机会,偏偏又因时间偏差,擦肩而过,于是,我与他之间交往的亲密度便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更能够在不远不近处观察他、体味他,并通过表象与内在的举止言谈去剖析他,研究他。对他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我不想按照惯例浓墨重彩、锦上添花地大肆渲染,而是以一种“君子之交,淡淡如水”的心态去解读他、描述他,这样的文字往往会更客观、更理智、更可信、更少有导向偏移的个人色彩。
谁抓住时代 谁就拥有财富
这是一句极为经典的话,从许四海嘴里讲出来更显得意味深长。
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某一个历史阶段,譬如改革开放,有人抓住机遇扬帆起步、兴旺发达了,有人逆向而动、败落颓废甚至丢失了自己。比如“文化革命”有些人随波逐流,万念俱灰,不再思进取,许四海选择了紫砂壶,而且一旦上路,便矢志不移,数十年从没改变,焉有不成气候之理?
许四海于1964年当兵参加越战,1969年回来,许多战友牺牲了,这种悲痛迷茫的情绪,没有在他脑海里停留太久,很快把沮丧的心情转化为一种动力、一种爱好,他选择了藏壶。当时他所驻守的地域受潮汕影响,都爱喝茶,当地人讲,用玻璃杯是喝,用紫砂壶是品,有人告诉他:美国在广岛投原子弹时,喝茶的人跟不喝茶的人受辐射伤害是大不一样的!于是他开始学着品茶,那时一把壶块儿八角,一般人还买得起。1969年他在地摊上看到一把老壶,要价几十块,可是他没那么多钱,就摘下手表想换,人家不干。他实在没有更值钱的东西,干脆一甩头把身上的毛衣脱下,摊主被他感动了,老壶便换给了他。他非常高兴,拿回去左看右看看不够。这把手表加毛衣换回的壶,便是他生平收藏的第一把老壶,晚上干脆就搂着老壶睡觉。待1980年转业时,他手上已有四十多把壶了。嗣后到地方,在上海当了三年半科长,大画家唐云的外甥女恰好在他的科里,通过这层关系,他很快结识了唐先生。这位有上海唐伯虎之称的大画家,不但书画超群,同时也酷爱紫砂壶。一次唐云拿出八把“曼生壶”,一把一把地给他讲,许四海一把一把反复把玩,真真切切地爱不释手,从脑门到手心都沁出了汗,兴奋到了极点。唐云说:“中国不缺科长,缺的是制壶大师”。这突如其来的醍醐灌顶,让许四海茅塞顿开,他毅然辞去公职,去宜兴紫砂二厂当副厂长,一干就是两年。1986年返回上海,他再一次抓住时机,决定自己干了。

这一次大转移,他把好多东西,包括不少名家书画全都丢掉了,唯有不惜重金收购的紫砂壶,一把都不少。他知道历史上留下来的壶,一把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打碎了,他听说一位如他一样搂着壶睡觉的老者,老婆叠被子用力一抖,被子上的壶掉在床下,摔了个粉碎。每一把老壶能存留下来都太不容易了,这是他再次创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一把老壶可以给收藏家提供鉴赏标本,一把老壶可以为制壶人提供制作的样本,不断制作出新壶,便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他开始亲手制壶。做紫砂壶看着容易,制起来却很难,一壶一传奇,一壶一世界。很多紫砂壶可能看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的阅历和收藏达不到一定程度,便不可能接触到一定数量的大师作品,更不可能做出上等的好壶来!紫砂鉴定为什么难?因为制壶者大都是从贫困中过来,以前的不了解而造成认识上的误差,更多的收藏家与市场脱节,真正入门的不多!不摸到两三千把壶便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事紫砂行当的人文化水平都不太高,许四海充分认识这一点,在制壶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如饥似渴地吸纳各类营养,抓紧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他有幸拜在书画大师唐云门下。唐云从“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讲起,讲他精篆刻、善书法、工绘画,为官一方,闲云野鹤,一位浓郁文化气质的县令,他设计的壶被后人称为“曼生壶”,从历朝历代的万千县令中脱颖而出,留名史册。唐云还讲到:一壶在手,喝茶可以清心明目,把玩可以窥视壶里乾坤。中国人的紫砂壶在世界上堪称一绝,集书画、诗文、篆刻、雕塑于一体,不施釉彩,以素面素心立身,令人把玩时遐思无限,只可惜老祖宗传下来的紫砂壶历经劫难,能够留存在世的已寥寥无几了。
一片冰心在玉壶。大师的谆谆教导,点点滴滴,潜移默化,融进许四海的血液里,歌曲里唱的“千年等一回”,他等到了。他感受着一种责任,一种抱负,谁抓住时代,谁就抓住财富。许四海不失时机地振翮展翅,他要起飞了!
不交学费当不了收藏家
许四海挂到嘴边的几句话是:“要敢交学费,过手的多了,就炼出了火眼金睛!不交学费就当不了收藏家!”四十多年来,许四海看过紫砂无数。上海是紫砂壶的桥头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峰时,宜兴及海外的大量紫砂壶流进上海。国民党的原高官黄振雄搞了一个“百人百壶展”,其中也有许四海的一把,让无数观者大开了眼界。当时经营紫砂壶的人不少,但大都是从经济着眼,著名的有“四小龙”、“八大块”等等,不少人赚钱,也有不少人赔钱甚至血本无归,这中间的界线就是买真买假了!
许四海也交了不少学费,真金白银换回了任何书本上不可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积数十年之功,他总结出了“五力”,即:一要有智力,善动脑筋;二要有眼力,久经锻炼;三要有体力,往返奔波,艰苦的差事;四要有财力,经济支撑,不做空想;五要有魄力,关键时刻,敢于拍板。比如碰到“大亨壶”要有倾家荡产的气魄,不惜一切,势在必得!
有了这五“力”,才有了后来的“大亨壶”传奇。当时顾景舟一把壶才不过几百元,邵大亨的要两三万,许四海放弃顾景舟而直取邵大亨,没有大胆的魄力,果断的决定,便不会有后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人世间的事,其实是非常自然而公平的,不管交了多少学费,许四海在得到“大亨壶”的一刹那间,他所有的付出和损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加倍地补偿回来。
大亨壶
说起“大亨壶”的获得经过,传说中有几个版本,但邵大亨的故事从许四海嘴里讲出来,就比书刊上描写的要生动得多。
邵大亨是清代一朝制壶高手,闻名天下。有一年中秋他邀几个挚友乘船赏月,行之中途,忽闻泊在岸边的花船上传来阵阵惨叫。他忙叫船夫去打探究竟,一会船夫回来告诉他,苏州来的巡抚大人正在船上游宴宾客。这巡抚有爱壶癖好,刚弄到一把好壶向客人炫耀,却被小丫鬟泡茶时不慎打碎,一怒之下将小丫鬟吊起来毒打,还要把她扔到河里。邵大亨闻听怒火中烧:“什么狗官?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把茶壶?”船夫说:“这把茶壶可不一般,是鼎鼎大名的邵大亨做的。”邵大亨听了提着随身所带箱子去会巡抚。见过面,当众打开箱子,满船人傻了眼,一箱子茶壶,把把都是邵大亨所做。邵大亨对巡抚说:“你随便挑一把,条件是把丫鬟放了!”巡抚喜出望外,假意推让后挑了把壶,随即放人,并请教邵大亨尊姓大名。邵大亨冷冷一笑:“大人爱壶胜过百姓性命,你失而复得大亨壶,不必再问在下姓名!”说完拂袖而去,回到自己船上,越想越不是滋味,突然打开箱子,将所有茶壶抓出来一个个摔得粉碎,统统扔进河里,船上的人惊愕不已,邵大亨感叹地说: “想不到我做的茶壶差点害人性命,这壶看来不能再做!”随即“金盆洗手”了。所以邵大亨的传世作品极为稀少,也就越发显得珍贵。
丁蜀镇潘家正藏有一把“大亨壶”。工艺师李昌鸿告诉许四海,他亲眼看过《宜兴县志》记载着这把“掇只壶”。当时就有“一壶千金”之说。清末民初,潘家是丁蜀镇上显赫的人家,这把壶原是邵大亨为潘家先人特制的传家之宝。传到第三代,也就是如今持有者的父亲,解放后到东北哈工大读书,1957年被划为右派,生活苦不堪言,把随身带去的十几把精美紫砂壶都换成吃食,唯独剩下“大亨壶”舍不得卖。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疯了,被遣返原籍,这个疯子将最后一把壶用破棉絮包了回来。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此壶历经劫难竟然没有半点损伤。嗣后,这把神奇的壶躲过“文革”。他的主人黯然辞世,破败的家需要支撑,第四代的年青人就想到了“大亨壶”。说起来顾景舟的母亲属邵大亨一支,于是最早是顾景舟拿到家里,看了三个月,准备拿自己的多把壶交换,潘家不愿意。随之徐汉棠又拿去十八天,提出用他的几把洋筒壶换,潘家也不答应。这时,吕尧臣得到消息带着许四海去拜访潘家了。那是一个夜晚,在潘宅大院的天井里,许四海看到天上是星星月亮,下边是这把令人神往的“大亨壶”,通体圆润,大气磅礴,无论从造型、比例、平衡等各个方面都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表面包浆如玉一般晶莹,散发着淡淡的光芒。许四海情不自禁地想上前摸一摸,被潘家的小青年拦住了:“只许看、不许碰!”许四海只好问:“有毛病吗?”“没毛病!”许四海问他:“多少钱可以出手?”小青年说:“这壶是没有价的!”许四海说:“潘师傅既要转手,心里总得有个底吧!”小青年想了一想说:“那就三万吧!”话一出口,许四海吓了一跳,半天说不出话。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的月工资才几十块钱,三万元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许四海越谈价,那小青年就越看透了他的心思,于是死咬一口价,一分钱不让。最后许四海横下心说:“好!三万就三万!”正巧这天上海有朋友在宜兴活动,当天返回,许四海就让捎信给太太金萍珍赶紧凑三万元星夜送来。金萍珍以为老许出了什么事,急着四处借钱,当夜租了个破得不能再破的车,抱着三万块钱心急火燎地赶到宜兴。但第二天把钱送到潘家,小青年反悔了。许四海生气地问他原因,他又说不上来。后来才知道,潘家听说香港、台湾人能出高价,是想把壶拿去上拍卖会。而金萍珍得知这么回事后,也大发脾气:“你买壶买疯了?一把壶怎么也不值这么多钱哪?再说钱都是借的。买了壶日子还过不过?你拿什么还债呀?”然而钱到了许四海手里,太太再发火也没有用了。六月份开拍,许四海和“大亨壶”一块进到了拍卖场。潘家的算盘打错了,原以为港台客能出高价钱,不料香港客只出到一万六,许四海出到两万三,没人再举牌了,于是落槌。小青年无奈之下亲自把壶送到许家。第二天报纸大标题登出“大亨壶易主”,他三万不卖,而许四海两万三却拍到了手,即使这样两万三在当年也不是小数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顾景舟一把壶几百元,两万三能买多少把顾景舟制的壶啊?许四海少拿了七千元,却又给了潘家不少名人书画,也算做了补偿,皆大欢喜。
半年后,有人愿出八万要许四海转让这把壶。一年后又有一个台湾养狗发家的“狗司令”,干脆把二十万现金拍在他桌子上。到了1992年,一个台湾古董商出价一百八十万,都被许四海一一谢绝。他说:“别说一百八十万,一千八百万也不卖!这是民族遗产,国家的宝贝,到我手里就不会再流失了!”到 2010年,北京还真有人出价两千万,已超过当年许四海随口说的一千八百万,但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不屑一顾,金钱的多少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按许四海自己的话说:“自从有了大亨壶,我的事业早已蒸蒸日上了。”
 万壶
万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