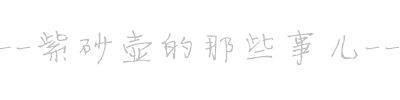—闻亢

中国的手工艺制造业起源很早,有籍可考的大略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间,据说墨家大多就来自于小手工业者。工艺品当然首先是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工匠们在口手相传的过程中,制作技术不断提高,最终使其既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又具有了一定的艺术性:也就是说既能给人们生活带来实际的方便,又在一定程度上让使用者或观赏者得到审美的愉悦。宜兴紫砂壶正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一个杰出代表。
综观紫砂壶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紫砂工艺正是沿着上述两条道路在探索和发展。一方面,无数的紫砂艺人在制壶的技术层面上不断创新,比如从金沙寺僧和供春的捏制坯胎、挖空内部成型到时大彬的拍身筒、镶身筒成型法;从前人的人缸烧壶到李茂林的匣钵封闭烧法。这些技术的进步无疑为紫砂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实用的基础上,艺人们也在如何使紫砂壶更具审美艺术性上孜孜以求。历史上有两个人在紫砂壶艺术性上的探索贡献最大,一是时大彬,他摒弃了前人的匠气,突破了供春的大壶范篱而多作小壶,使其更符合文人的审美情趣;二是陈曼生,虽然他不是制壶艺人,但作为一位在诗书画印等方面有极高造诣的文人,他是极其熟悉中国传统审美特征的。他积极参与紫砂壶的创作且成果斐然。”曼生十八式”的造型设计和整体上的文人化装饰,极具美感,无疑在紫砂壶历史上是具有突破性的,他的影响绵延至今日。
现在单讲紫砂壶造型上的艺术美。美的本质是什么,东西方哲人多有论述。古希腊人认为美就在物体的形式,具体地说,只在整体与各部分的比例配合上,如平衡、对称、变化、整齐之类。因而古希腊人说”和谐”多于说”美”。比如,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就很少用”美”字来形容文学作品,他还认为和谐感和节奏感是人爱好艺术的原因之一。在西方也在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比如英国哲学家休漠就说:”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里见出一种不同的美。”当然他并不否认美与”对象各部分之间的秩序和结构”有关,只是肯定对象的形式因素要适应不同人的特殊审美心理,才能产生美感。由此我们可以说,欣赏者觉得一个工艺品是美是丑,与工艺品本身的造型是否合乎一般美的规律和欣赏者自身的审美趣味有关系。
作为中国传统工艺的紫砂壶本身根植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又加上历代深谙中国审美特征的文人的积极参与,因而,它的造型艺术是无法摆脱中国传统美学影响的。当然,欣赏者如果不能对中国艺术的审美特征有所了解的话,是很难在更高层次上欣赏紫砂壶的美。那么中国传统的美学特征有些什么具体要素呢?简言之:一、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比如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即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该志向于道,立足于德,归依于仁,游憩于艺术园圃之中,最终通过艺术和审美,使精神进人自由境界。二、突出实与虚的转化,认为艺术作品的虚实相生会产生一种气韵生动的审美意境。三、注重形与意的关系。重写意而不杏弃形似,肯定理性与直觉统一,但偏重于直觉。这些审美的倾向在紫砂壶的造型设计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比如:美与善的结合就要求工艺师在制壶时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认为美的造型而有损于它的实用功能:在壶的身筒与钮、流、把、足的空间搭配上除了考虑实用功能外,如何使它们之间虚实相生则是考验一位工艺师水平的重要标准:形与神的关系处理 不好,有些”花货”就会只有形似而缺少生活的趣味,筋纹器对实物的绪象化处理的水平则影响到作品盛否能形神兼备。
所以,历代优秀一触萦砂壶作品大多是实用性极佳而又充分体现造型美的一般规律传统审美情趣的能使欣赏者,尤其中国欣赏者产生审美的愉悦。
具体到紫砂壶的造型设计,本文准备略略谈几个”相对”而又”相成”的审美范畴,因为形式美的最基本原则即在于寓变化于整齐,对立中求统一,使壶的整体保持平衡。这里要强调的是平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自然资源的平衡。好比一个站着的人,就没有失去重心的问题,肯定是平衡的。因而这是一种规则的静态美。第二种是非对称的平衡。上下左右并不相同,可是在视觉上又能给人平衡的感觉。好比一个运动员,在运动中保持平衡,动作难度越高,越需要技巧。这是一种富有变化的不规则的动态美。紫砂壶中既有对称的平衡,也有非对称的平衡,且以后者为多。也正因如此,更体现了紫砂壶制作的难度。
准备谈的范畴是:一、曲与直,二、方与圆,三、骨与肉,四、繁与简,五、实与虚,六、形与意。
一曲与直
中国的艺术审美和西方有一点很不同,就是非常重视线条,无论雕塑、绘画、书法还是建筑。米开朗基罗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就是从山上滚下来也滚不坏的,因为他们的雕刻是团块。中国传统艺 术就很不同,我们特别重视线条, 这可以在汉代的玉雕,初唐佛像造 像的衣褶和历代大量的浮雕作品 中得到印证,它们不注重立体性, 而注意流动的线条。尤其中国产生了纯粹的线条艺术—书法,更是说明了线条在中国人审美心理上占据的重要地位。当然,审美意义上的线条绝不是任一自然线段,而是使形体演化成为或飞动或端庄的审美感受的重要方式。
那么线条有什么样的审美特征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简约;二、变化。简约就是指线条是最简单、概括的艺术表现手段,这与人类的艺术创作发展的过程有关。上古人类在认为和表现世界的过程中,难以用繁缚语言或其他手段作准确的反映时,往往采取一种概括、模糊的抽象手段,于是他们创造了最简约的线条。古人认为线条符号愈简约,愈能包容复杂的内涵。《老子》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甚至有时就把”一”等同于”道”。而线条就简单到”一”。八卦的卦象也正是由线条的不同变化构成的。正是这种简约而包容的特征给艺术创作者提供了寄托和浓缩情感意绪的无限空间,也给欣赏者提供了自由思考的无限空间。变化又使线条成为了艺术作品中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说简约使”万物始于一”,变化则”一生万物”。比如:有了线条的简约性才有筋纹器对实物进行抽象化概括的可能,也正是线条的变化使紫砂壶具有了形态各异的造型,同时壶体上装饰线条的变化更使紫砂壶有了千变万化的审美效果。
运用到紫砂壶上的线条主要有两种,即:曲线与直线。
先说曲线。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德国的文克尔曼研究了古代雕塑的线条之后得出一条结论:一个物体的形式是由线条决定的,这些线条经常改变它们的中心,因此决不形成一个圆形的部分,在性质上总是椭圆形的。这就是说,美由曲线形成,但各部分曲线不宜围绕同一圆心,也不形成完整的弧线而是”椭曲线自然流畅,颇有动感且干净利索。可能正因为陆思亭在这壶型上曲线的成功运用,才使其成为一个特定的形制名称吧,这是身筒曲线的运用。有的壶型流的曲线与壶体和提梁也能形成美妙的曲线,比如顾景舟的提璧壶,整个壶体呈扁圆柱形,而正是这样才使流的微曲线恰好与壶底曲线流畅地贯通,而且这种贯通的”势”似乎并没有停止,反而给人感觉直冲向上又与提梁的曲线相连,并重回到流的根部,完成了一个曲线的循环,尽管身筒的底部曲线与提梁没有直接对结。这把壶的曲线运用可以说是极其成功的。我们可以想见,顾大师在设计时是怎样从整体的和谐出发而又在制作时怎样的一气呵成,否则就不可能达到这样气韵生动的效果。这种设计思路达到极致的是张守智、汪寅仙的”曲壶”。这把壶的造型主要就是两条曲线的展开,而且这两条线将壶形的各个部位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了强烈的旋转各个部位有机地融为一体,产生了强烈的旋转韵律之美。这个壶形为艺人们在制壶时大胆运用曲线开了先河,影响深远。另外何挺初的”浪花提梁壶”也是成功运用曲线的典范,这里就不具体分析了,朋友们可以细细品味曲线之妙。
再说直线。不同的线型,给人带来的审美情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曲线给人舒畅、轻快的感觉,那么直线就给人以挺拔、向上的感觉。紫砂壶挺拔、硬朗圆的”曲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曲线是最有张力和流畅感的。它既没有直线的生硬,也没有标准圆弧的柔弱,正介于力度与弹性的中间点。由此延伸到紫砂壶上,曲线的运用就要讲究”度”了,用得好会使整体有种不失力度的流动感。否则,要么生硬、板滞,要么软弱无力。比如思亭壶:身筒两侧曲线,自顶部圆钮处流泻而下,壶盖处向外曲张,肩部自然向内弯曲,到腹部则又向外膨胀成一条更大的曲线,钮、盖、腹三段的气势神韵,从线型的角度也体现出造型的阳刚之美。
但是,在紫砂器中的直线不能僵直、板滞,而是在直线中寻求变化,以做到直而不板、轮廓分明、刚中见柔。值得注意的是造型中的所谓直线,不同于几何学意义上的直线。紫砂壶中的直线往往含有曲线的成分,曲线的长度有限、曲度也很小,并不影响线型的主体所形成的特色,却体现出刚中带柔的风韵。比如方壶通常会在钮、肩、流、把等部位用少许的曲线作为过渡,使整个器型既端庄雅正且又温婉动人,不使观者有过于棱角分明的视觉刺激。当然也有一些造型则大胆地把曲线和直线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不分伯仲,创造出和谐统一的审美效果。比如钟形壶、柱础壶、方钟壶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
线条除了在器型上起作用之外,在壶的身筒上也多有装饰。它们可多可少,可横可竖,可直可斜,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可轻可重,可阴可阳……随机勾化,变幻无穷。
总的看来,紫砂壶造型中曲线的运用是多于直线的,这或许是从实用性方面考虑的结果,毕竟壶是拿在手里喝茶的。
二方与圆
方与圆在艺术作品中的被广泛应用,除了因其视觉上独特的审美效果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中国古人”天圆地方”思想的影响。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并由此影响到中国人的审美倾向。比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就主要以圆形和方形为主,但似乎方器比较多些,大件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小件的有方爵、方斗、方尊、方罄、方击等等,不胜枚举。有趣的是这似乎和紫砂壶的整体状况刚好相反,后者恰恰是圆形壶大大多于方壶。我想这是紫砂方器的制作难度大和其实用性不如圆形器的结果吧。这种”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还渗透到大到建筑,比如天坛,小到玉琼和钱币的设计上。由此可见,方圆造型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深深烙印到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之中。
明白了这些,就会对紫砂壶运用方圆造型的巧妙有更深刻的体验了。
圆是最有弹性的几何形,它在紫砂壶的造型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几乎所有的壶形都有圆的踪影。人们通常对圆形壶外形的基本要求是”圆、稳、匀、正”,甚至要达到珠圆玉润的地步。实际上在圆壶中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珠圆”的,一般的情况恰恰是多个大小、弧度不同的圆形对照,比如邵大亨和程寿珍的掇球壶;有时是提梁和壶身的圆形对照,比如经典的大彬提梁壶;更多的还有圆形把圈与壶身的对照。
前面讲过纯粹使用方形来造型的紫砂壶不多,但这样说并不是指方形本身在审美上有什么缺陷,而是在成型工艺上较难把握罢了。但好的方壶总给人一种或挺括周正、坚硬利索的感觉。较为大家喜爱的壶形有六方提梁、八方提梁、合斗壶、方斗壶、砖方壶、亚明方壶等。当代名家潘持平则是个中高手。
圆与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无方就显不出圆。《周牌算经》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圆出于方,方出于矩”,这是说最初的圆是由正方形不断地切割而来的。所以在紫砂壶造型中通常是方与圆相交融的。正由于方圆在美感上迥然不同的特征,所以这类紫砂壶制作起来是最困难的,过圆则失之柔弱无力,或者臃肿含糊;过方则又僵硬生涩。这方面的代表壶型我认为是瓤棱壶。此壶形俯视呈四方形,侧面看又有覆斗状,但又不是直棱角的覆斗,像两条斜边向外弯曲的梯形。盖、颈是小四方而底部相比上部又大出很多。这样的上下变化全依靠自壶盖延伸下来的四条弧线的连贯与过渡。因此这对四条弧线的处理就成为此壶造型的关键,因为它影响整个壶身的方圆形状。再加上身筒基本上呈方形,而把又呈圆环状,所月桂珍伏止盘以如果把和身筒的方圆搭配不协调的话,也会使整个壶形显得极为别扭。
我们在资料上能看到明朝的李仲芳很完美地把握了此种壶形的平衡,创造出”方中寓圆,圆中见方”的奇妙境界。欣赏把玩此种壶型,我们可以边饮茶边静下心来做做方与圆的辩证思考了。近代黄玉麟也制有瓤棱壶(吴昌硕铭),很明显,在李仲芳的基础上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他把身筒上的四条弧形棱角线变得更加柔和,原来的近乎直线的流也改为三弯,把圈则更圆。总之,黄玉麟的设计增加了”圆”的分量,所以整体上给我们一种既端庄典雅又柔和圆润的美感。这种方圆融合的壶形还有清朝陈秉文款上方下圆的束腰方壶,现代则有高海庚设计的前方后圆的状虎壶。
由此可见,方与圆在壶体上的运用比例直接影响着紫砂壶带给我们的审美感受。
三骨与肉
我最喜欢的壶型是子冶石瓢。它的整个壶体巧妙地运用了三角形的对照变化,身筒与盖合为一个大的三角,把圈为三角,钮为三角,三足也构成三角,甚至直流与身筒也构成了”虚”的三角。这些三角更能巧妙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可以说,子冶石瓢是几何类型中运用三角形的经典之作。不过,器形的流畅与和谐还不是我喜欢它的根本原因。在把玩欣赏好的子冶石瓢作品时,我常常感到壶体中透出一种”骨力”,简洁利索、清奇脱俗。壶身内外氮氯着一种刚健挺拔的风骨,一种正直文人所特有的不同流俗、遗世独立的风骨。有时,我甚至偏执地认为子冶石瓢泡茶,我常常感觉是在和一位高士对饮交流。
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的审美趋向呢?或者说,在我看来为什么子冶石瓢的造型能带给我这样一种充满骨力的”感觉”呢?
我想到了审美心理上的一个重要概念—移情作用。美学家朱光潜说:人在聚精会神中观照一个对象时,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和情趣的外物仿佛具有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只有物理的东西也显得有人情。这样的例子在文学作品中是非常多的,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些诗句中的观者无疑和外物已难分解,似乎有”庄周梦蝶”的趣味。我想我与子冶石瓢的对饮或许有这么点意思。但有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就紫砂壶而言,为什么此型能使人产生此情而彼型则会使人产生彼情呢?若敬亭山乃荒山一座,李白还能看不厌吗?鸟儿的鸣叫若轻柔婉转何来”惊心”?由此我想,我们欣赏不同风貌的紫砂壶而产生的不同审美心理从主观上讲是移情作用的结果,而客观上紫砂壶本身的造型则给了我们”移情”的基础。
回到子冶石瓢这个”客体”,它是怎样给人”骨力”之感的呢?我觉得关键就是内在的整体骨架要清晰。因为骨是生命和行动的支持点,表现出内部的坚固支撑力,给人坚定的力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画者没能很好地通过骨架来表现虎的力量和气魄吧。联想到紫砂壶。如果内在的结构缺少力度,甚至模糊不清,整体必不能产生充满”风骨”的感觉。
当然只有”骨”而没有”肉”,就会给人一种干涩枯瘦的印象,若只有”肉”而没有”骨”又会显出臃肿无力的样子,当然也没有丝毫美感可言。经常看到有些所谓创新的壶形,流、把甚至身筒都无原则地加粗,简直”胖”得没道理!或许作者有其独到想法,但这样的壶形实在让我经常联想到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对于骨肉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拿中国书画来比较分析。书画中的骨力并非是剑拔弩张、横眉冷对,而是在笔墨间凝聚了一种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艺术家的内心。比如书法上有”点如坠石”之说,其实这”点”并非只是一个墨点,它的内部会发挥出一种力量。再如中国画的竹子,虽不讲究透视却也有充分的立体感,我们会感到一种骨力、骨气。同样,有骨力的紫砂壶给人的感觉是不仅”站得稳”,更要挺拔昂扬、精神抖擞的样子。”肉”是附着于”骨”之上的,”肉”要多少才恰到好处,那要看整体是否和谐、匀称、有力。就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由于他熟悉人体骨骼,因此造型中,我觉得筋纹器最能考验工艺师在骨肉关系处理上的能力。好的筋纹器既通过清晰的线条与方圆很好地使壶体挺拔有力,同时也拥有温润饱满的”血肉”。比如时大彬的菱花壶,欧正春的菊瓣壶,汪宝根的仿古葵壶,还有一些成功的如意仿古都能达到骨骼有力,血肉丰满的境界。
紫砂界的朋友经常喜欢用”骨肉亭匀”来形容一把壶既有内在风骨结构又有均匀丰厚的外部造型,我觉得这个词很好地诊释了紫砂壶造型中骨与肉的关系。
 万壶
万壶